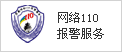第一,“煤改氣”要充分考慮近期的供應安全和遠期的運行成本。近期供應安全,從各方反應來看,自不待言。遠期來看,除鋼鐵業外,大量“煤改氣”乃是將北方的供熱鍋爐改造成為天然氣鍋爐,意味著未來北方的天然氣供應峰谷差將進一步增大(北京接近20∶1)。由于我國北方取暖季主要集中在冬季,但城市燃氣供應能力必須按照最大用氣需求進行配置,意味著全年大多數時間設備低負荷運行,浪費巨大。而且,在我國儲氣設施、調峰設施尚不健全的情況下,冬季高峰天然氣供應走鋼絲、高成本的態勢,會長期存在。動輒要求工業企業停產檢修,既有違契約精神,又對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行構成不利影響。此外,隨著我國天然氣對外依存度的逐步增加,能源的安全問題愈加嚴重。
第二,要充分考慮成本和效益。目前,“煤改氣”采用的辦法還是慣性思維,由政府強勢推進,一方面設定最高煤炭的消費量,另一方面對天然氣采暖、發電等實施補貼。盡管我國環境問題確已到了須用“重典”的歷史關口,但欲速則不達。一則,強令諸多仍運行良好的煤鍋爐、煤電“煤改氣”,本身就是巨大的浪費。二則,強令某個區域內禁止燃煤鍋爐的存在,實際上是某種“鄰避效應”在地方政府行為上的一種表現——污染可以在全國任何一個地方,但不要在我的轄區內。然而,污染是不受任何行政邊界限制的。這就要求我們從一個全局治理角度審視“煤改氣”投入的效用最大化,而不能單純著眼于某個單一區域。
各地強力推進“煤改氣”,實際上是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表現,并非治霾的長遠之策。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突出強調了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提出了要推進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推進天然氣等領域的價格改革,并明確劃定生態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我國治霾,推進“煤改氣”,應按照這一綱領性文件,有所為,有所不為。
第三,要充分利用市場規律和價格杠桿來推進“煤改氣”,讓落后產能退出和天然氣替代能夠平穩過渡,而不是一紙關停命令。要建立一套能夠反映天然氣、煤炭等能源產品的供求關系和稀缺程度的價格體系,并將各類能源產品負的外部性納入價格體系予以考慮,考慮其對生態環境損害成本和修復效益。
第四,要定標準,強監管。政府應通過制定比如天然氣行業長期發展戰略規劃,包括煤鍋爐(煤電)等用能形式的排放標準,并通過規劃、標準的執行來強化對市場的監管和違法的懲戒機制,以裁判員的角色而非管理者的角色介入市場。
第五,要打造交易平臺,利用市場化的方式做好區域協調工作。通過建立跨區域的天然氣交易平臺和碳排放、污染排放交易市場等,優化氣源配置,促進有限的資源流向邊際收益(包括經濟收益、環保收益等)最大的行業和區域。鑒于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傳統能源將長期居于主導地位,政府應給予傳統能源的高效利用、環保技術與新能源同等優惠的政策。

 在線客服
在線客服
 企業微信
企業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