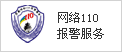“這標志著延續了20多年的半計劃電煤交易‘枷鎖’徹底放開,也是煤炭向全面市場化邁進的起步。”中國煤炭運銷協會顧問武承厚向《中國能源報》記者坦陳,“這是電煤價格走向完全市場化的重要一步,但絕非最后一步。”
指導意見重建新綱
舊制新綱代。2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有關負責人就深化電煤市場化改革一事表示,建立電煤產運需銜接新機制是此次改革的重點和亮點。
一是在電煤產運需銜接簽訂合同中,不再區分重點與非重點,創造企業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環境。二是取消了價格雙軌制,電煤全部實現市場化,尊重市場規律。三是國家不再下達年度跨省區煤炭鐵路運力配置意向框架,銜接中進一步減少了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行政色彩,維護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四是對落實運力的合同由國家發展改革委、鐵道部、交通運輸部備案,作為日常監管的依據,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除此之外,指導意見還提出了加強煤炭市場建設,繼續實施并不斷完善煤電價格聯動機制,推進電煤運輸市場化改革和推進電力市場化改革等四個方面的主要內容。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指導意見在煤電聯動機制上進行了8年來的首次調整:監控調價周期由原來不少于6個月調整為一年,延長了周期;電力企業消納煤價波動的比例由30%調整為10%,減輕了火電企業的負擔。
上述負責人強調,推進電煤市場化改革應遵循“堅持市場取向,促進公平競爭;堅持循序漸進,實施重點突破;堅持依法行政,創新管理方式;堅持統籌協調,兼顧各方利益”的重要原則。
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盛贊該指導意見的出臺為“近年來我國能源領域最有意義的改革”。
行政干預的墻仍若隱若現
煤電“新政”可圈可點,但并非無可挑剔。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電力人士向本報記者直陳,指導意見存有兩個重大缺陷:其一,在中長期合同方面未就交易量、期限價格、金額等做具體規定,企業之間亦無共識;其二,煤電聯動的前置條件之一“電煤價格波動幅度超過5%”,其價格參照物自政策誕生之日起至今缺位。
“如果不能建立起基于科學依據的全國煤炭價格指數,煤電聯動未來仍然難以落實。”上述電力人士表示,一直以來,煤電聯動都沒有明確煤價波動依據。“是合同價還是執行價,是坑口價還是到廠價,是下水煤還是直達煤?”
參與過此項電煤價格變化測算工作的原中能電力燃料公司總經理、中電聯燃料分會會長解居臣曾向本報記者表示,電煤價格具體漲了多少算不清楚,就是過去數次煤電聯動遲遲未動的原因之一。
上述電力人士稱,各種煤價差距之大,早已形成“灰色地帶”。比如從出礦到電廠,中間環節造成價格差異高至數百元。“這個依據不說清楚,將來國家還是想調就調,給行政操作留下很大空間。”
至于電價調整周期有所延長似乎有違電力市場化方向,該人士反而十分坦然。“只要條件滿足時及時調整,周期長一點并不要緊。”
事實上,電力的擔心,煤炭亦不能置身事外。
在完善調控監管體系方面,指導意見指出,在電煤價格出現非正常波動時,將依據價格法有關規定采取臨時干預措施。如何明確“非正常波動”的范圍和“臨時干預措施”的規則,武承厚認為至關重要。“是基于科學依據(如依據某種煤炭價格指數)、有公信力(如價格聽證)的指導性調控,而非主觀的干預嗎?”
上述電力人士還透露,指導文件所稱“此次電煤價格并軌后上網電價總體暫不作調整,對個別問題視情況個別解決”,其“個別問題”的判斷標準原則上是指重點合同煤和市場煤價差比較大的省(區)和重點合同煤使用比例較高的熱電廠。
依此標準,價差較大的地區主要包括山東、黑龍江、重慶和四川,但重點煤使用比例較高的熱電廠則沒有清晰界定標準。“事實上,這又是一個可運作的空間。”
除此之外,指導意見中“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對煤電企業正常經營活動不得干預”的要求短期內也無法消除。28日,內蒙古鄂爾多斯宣傳部外宣辦負責人陳曦就緩解該市煤炭市場低迷狀況事宜稱,目前該市已啟動了調控等各項措施,試圖突出重圍。其實行“以銷定產”的具體舉措之一便為:供應煤票。多年來,山西亦以這種方式管理省內煤炭生產和流通秩序,無票不得上路。
對此,中國煤炭工業協會政策研究部副主任張宏向本報記者稱,“這還需要一個過程。”但具體是多久,他并未給出清晰的答案。
五大電力相關負責人向本報記者表示,在多年行政干預之下,電企已經喪失新建火電機組的動力。并預言2103年電力供需形勢將向結構性短缺轉向結構性過剩,而火電新增機組裝機比例將下降至40%以下。
“這份指導文件未解決電價的歷史欠賬,也未解決歷史欠賬中的累計虧損。”該電企人士稱,“從2008年至今火電企業掛賬債務已有1000億元,盡管財政部這兩年已經向五大電力補充資本金200億元,但這遠遠不夠。”
但上述人士也表示,總的來說,這份文件斷了火電企業調整煤價的后路,勢必將增強電企業要求推進電改的意愿,“電力市場化改革被再度推至前臺”。

 在線客服
在線客服
 企業微信
企業微信